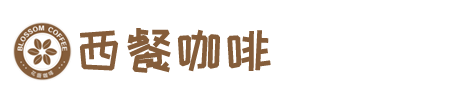天雨茶餐厅 小城诗意:酉阳的诗小城故事多
小镇诗:酉阳诗人
粞
有人说,如果以“县”为单位,放眼整个中国文坛,酉阳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现象。 就重庆而言,酉阳文学足以构成重庆文学的重要一极,甚至说它占了重庆少数民族文学的半壁江山也不为过。 而酉阳诗人层出不穷,就像酉阳山里的土豆一样,“一窝又一窝”。 他们从酉阳出发,即从酉阳历史文化的深处,从实体的酉阳和虚拟的酉阳,从有形的酉阳和无形的酉阳出发,肩负着各自的使命。 穿越时光、穿越风景、穿越文字,给小镇增添了无限的诗意光彩,丰富了他平凡而独特的生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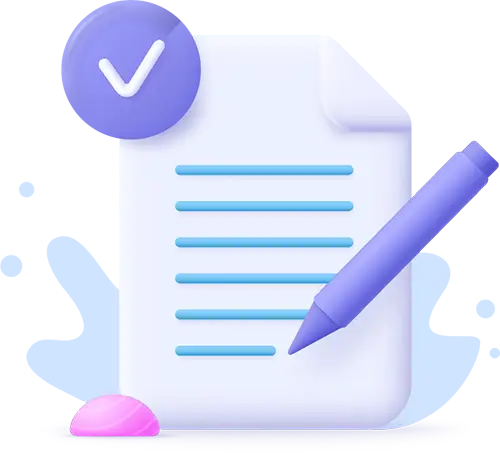
1、土壤说:“风一吹,帕尔毛摇曳。”
酉阳文学的现象性存在是有其深厚的基础的。 这里历史悠久,文化底蕴深厚。 800年来一直是州府所在地。 建立县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。
小学毕业后,我考入了当地最著名的学校——酉阳一中。 更名前,学校名称为四川省第五中学。 这可以追溯到赵世炎就读的桂花园小学。 酉阳一中桂花园文学社由此得名,其杂志《桂花园》现已蓬勃发展。 我所在的定市,辖9个乡镇。 当我考入酉阳一中时,定市共有五人入学。 平均来说,两个乡镇只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考试。
酉阳一中所在的龙潭镇,繁华繁华,平地数百里。 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龚滩古镇并称“千公潭霍龙潭”。 20世纪40年代,这里被称为“小南京”。 进入一中后,我如鱼得水。 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报刊都由图书馆订阅。 在此之前,我看过的课外书仅限于父亲留下的几箱马克思、恩格斯、莱尼斯选集,厚如砖头,无法移动和阅读。 世事变迁,需要有准备。 许多年后,我听说我获得了马奖。 图书管理员陈跃华先生还记得那个经常去图书馆的孩子。
彼时,文学热潮如火如荼。 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学校里,大学里、中学里,文学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 席慕容、王国真、琼瑶遍布大江南北。 “一大展”和“三兴”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诗坛。 看来那是一个民族文学的时代。 我还记得读到“既然我选择了远方/我只关心风雨”时的激动和震撼。 阅览室的杂志常用金属条固定在阅览桌上,《青年文摘》常选用王国桢的诗作。 发表诗的页面总是被不同的人反复阅读,留下深深的汗痕。
在众多杂志中,有一本杂志很特别,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,那就是《星星》。 我仍然记不起身份证上我家的具体地址,但我清楚地记得“红星路二段85号”。 有一次在新疆开会时,沙湾诗人麦丽红招待客人。 席间有人提到了同样的经历,大家都表示同意。 这些诗在细长的格式中像露珠一样清新。 突然有一天,我读到了《星星》中一组描写雪域高原的诗,心里感到高兴。 其中一句台词大致是“宝贝们在雪地里接受教育七天七夜”。 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,原来诗还可以这么动人。 文学如星,诗歌如星,彻夜闪耀。 我看了作者:冉仲景。 在我看来,冉姓是一个熟悉的、特殊的、罕见的姓氏。 这个姓氏在中国大概只有几个比较集中的地区。 在酉阳,冉姓是最常见的姓氏,居住人口超过20万。 我当时就想,这个叫冉仲景的人莫非是酉阳人?
当我这样想的时候,我并不知道这个叫冉仲景的人在康定师范学院任教,而他的父亲冉光荣是我的语文老师。 初中三年,每次上课,冉光荣老师总是在口袋里揣着一瓶酒,拿出来喝了一口,然后继续他生动的讲课。 后来,这个叫冉仲景的人从康定回到酉阳一中,从一个酉阳人变成了另一个酉阳人。 十几年后,他两次成为我的同事。
大约一两年后,我已经上高中了,我在论文纸上写了几首诗,寄到“红星路二段85号”。 发表了两篇,一篇叫《太阳在头顶》,另一篇叫《雪后阳光灿烂》。作者旁边加了括号:(中学生)。学校放置和往常一样在阅览室看,我小小的虚荣心可能就是从那时起就被激发了。
在众多的报刊中,还有一份报纸比较特别,那就是《酉阳报》。 本报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新华社酉阳分社。 《酉阳日报》在一中的特殊地位来自于每期都挂在阅览室门口的柱子上。 当然,学生阅读《酉阳日报》时,主要是阅读副刊。 如果某期有我校师生的文章,周围的人就会大幅增加。

20世纪80年代,创办了规模较大的文学刊物《游水》。 四十多年来,源源不断地流淌成生生不息的文化脉络。 我高中的时候,还有一群人在酉阳的另外两所大学读书。 陈小勇(叶海饰)在酉阳二中就读高中。 方舟、张元伦、向青松(二良春)、宋明德、马二,以及后来的何春华就读于酉阳师范学校。 当时,二毛是酉阳师范学校的一名老师,但教书的二毛当时并不叫二毛,而是叫牟珍珍。 只有写诗做饭的二毛才叫二毛。 此时,李亚威也从定城调到了县城。 冉仲景离开一中调到县城后,酉阳一中成长了一位新教师、作家彭欣。
当时,酉阳师范学校是一所著名的百年名校,也是该地区的最高学府。 潜江、彭水、秀山、石柱等周边区县的教师和党政干部大部分出自该校。 这群人各自习武,互不相识。 多年后,他们“胜利重逢”。 有一次,张元伦、向青松、马二三人相约回母校。 吃完晚饭,一群人吃夜宵。 即使凌晨三点商店关门,他们仍然不肯散去。 他们在街上从南到北,从北到南走着,直到天亮后才消失,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。 我不记得我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。 多年以后,当我回首过去,我已经分不清我的生命是被文学耽误了,还是被文学成就了。 唯一的解释只能由文学来规定。
说起冉姓,就不得不提冉土司。 酉阳经历了十多代土司。 几乎每一位土司都是一位颇有造诣的诗人,无一例外,都留下了大量的诗作。 今天我们正在编辑一本酉阳诗集,冉土司家族的成员有二十多人。 同时,当地较小的土司,如彭土司、天土司、白土司等,也不时有著述。
然而,酉阳真正的诗人却在民间。 无论是唱歌、跳舞、绘画、吟诗作赋,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开车卖浆的人,在酉阳,热爱文艺的人总是纷纷挺身而出。 有一种夸张的说法,在酉阳,只要会走就可以跳舞,只要会说话就可以唱歌。 “向天撒一把芝麻,这里就有万首山歌”。 这里所说的唱腔,就是酉阳民歌。 酉阳民歌都是即兴创作的,模糊成篇章,大多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写。 最难忘的一首歌叫《风吹,帕尔玛摇晃》。 每个歌手都是诗人,每首民歌都是诗。 一位诗人曾说过,当他看到酉阳民歌时,突然感到羞愧。 他几十年来一直在写诗,但都是徒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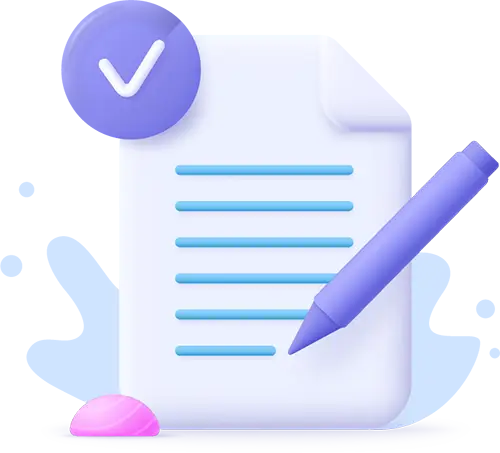
2、石宇说:“等樱花落了,我就去远方。”
小镇的生活单调而孤独。 文友诗人的聚会无外乎两种:一种是吃萝卜白菜鸡鸭鱼,一首诗一杯酒,或者是长话连篇。 睡不着的人拖着影子回家,孤灯清影,“困意来了”,就翘脚倒地睡着了,鼾声如雷; 另一种是在乡村里行驶,在荒坡荒山上,带着残山残水,说无论走到哪里,无论走哪条路,直到夕阳西下,余晖渐渐落下。 路穷了无路可哭,路穷了有归路。
除了线下聚会之外,当时线上交流也很流行。 那时,论坛蓬勃发展,QQ还是个新鲜事物。 敲着键盘彻夜不眠的人,除了玩游戏、聊天,还逛文学论坛。 小城镇里喜欢写作的人,除了国内著名的论坛外,还经常去当地的桃花源论坛。 潜水、看屏、主持人等词都是新词、热词。 很多人都是先在网上认识,再到线下认识。 有的成为了好朋友、知己,终生的友谊,有的则如飞蛾扑火,在光明面前死去。
20世纪90年代,小镇文友们的线下聚会场所通常是一家叫风之翼的酒吧,在那里吃饭、喝茶、聊天,最重要的是,可以在大屏幕上朗诵诗歌。 那时,人人正值风华正茂,俊男靓女,青春澎湃。 文学启蒙运动由此开始。 现在风之翼早已关闭,但建筑还在。 每次路过它,都感觉就像昨天一样,就像路过一片废墟。
后来,猫美书吧和今天的酉阳在线乘风破浪。 茂美书吧本质上是一个谈话吧。 许多文学沙龙、头脑风暴、诗歌朗诵、新书分享都在这里举办。 还有很多纸牌游戏、棋牌游戏、晚宴等。 毛梅书吧经营了几年,最终因亏损而关门。 不过,毛梅书吧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人创作并出版了一本诗集,名为《献给毛梅的99首致命情诗》。
有一段时间,刀锋在城南的山林里开了一家民宿,一边写诗一边填饱肚子。 她的诗和她的名字一样犀利,大多数时候只在她家的阳台上发表。 刀锋丈夫杨胜新是一位书法家,也是一位真正的厨师。 她家的巨大阳台既是餐厅又是沙龙。 多大可以打羽毛球? 周围环绕着玫瑰花的栅栏。 这家餐厅独临大山,百里山峰尽收眼底。 看着眼前的山丘沟壑,心里松了口气,后来这里就成了大家的新“家”。 同时吸引了来自潜江、铜仁、秀山等地的众多文艺青年前来打卡,他们的热情点亮了山村松林的黑夜。 然而,这家民宿最终因不通公路、过于小众、超出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而关闭。 夫妻俩反而在山下街开了一家九九重庆面店,生意红火。 诗与现实有时看似隔着一条小山路,但实际上却可能相隔万里。
时代在变,聚会的地点总会在几次镜头后发生变化。 后来我们把见面地点改到了倪月友家。 倪月友的家在阳光谷,周围很安静。 他的两个孩子正常上学,没有受到打扰。 最重要的是,他的妻子是天涯的一手好厨子。 柜子里还有很多自酿的酒,品种齐全。 仙人掌、杨梅、猕猴桃、大枣等。 有的人从阿蓬江带来了青青的百吉饼,有的人从黑水里带来了山大闸蟹,有的人从家里带来了红酒,有的人从肚子里倒出了隐秘的往事; 有的喝醉了,不省人事,大声尖叫。 睡觉时,他们不断地胡言乱语。 有人滔滔不绝地谈古论今,也有人喝得醉醺醺的,请了几人布下龙门阵。 突然有一天,我在手机上读到一首刘念的诗,名叫《邀请》,我觉得这首诗很应景:“明天最好,山谷里的樱花盛开了/虽然有只有一棵树,姿势很美//第七天也可以,可以赏花落/别再等樱花落了,我就去远方。 后来我想把它抄下来贴在倪月友家的门上,当一个人手里有很多青春的时候,他往往会肆意地挥霍,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才知道青春是宝贵的,是无敌的。但话又说回来,没有被挥霍过的青春未必就是真正的青春。
酉阳市位于重庆市东南部,武陵山腹地,与贵州、湖北、湘九区县接壤。 一出门,一不留神就到了外省。 四省市、边境地区山水相连,人员往来便利。 文友、友人、诗人亲如一家人。 最常来这里的游客是重庆的武隆、黔江和秀山,贵州的松桃和德江,湖南的凤凰和湖北的来凤。 有时贵州待客,有时重庆东道主,大家欢聚一堂。 这种聚会常因武陵山而得名。 路出武陵,山水豪气。 潜江的马耳、秀山的秦集、铜仁的摩尾、德江的王桥,都是温暖人心的古道。 马二甚至被称为潜江市的小松江。 每当有读书人经过钱江,马二都会抓住他不放。 便以美酒佳肴招待他,直到他喝醉了才回来。 他会留下诗词、字画,然后才放他走。

那年,第六届重庆文学奖在濯水古镇颁奖,酉阳不少人获奖。 获奖者陪同获奖者一行人前往古镇。 这期间,有好心人问:“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来领奖呢?” 我们只好笑着说,我们都是来看热闹的。 马二照例设宴招待宾客,并与他人较量。 看来得奖的是他,而不是其他人。 有朋友从远方来吗? 这句话在马二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世界的温暖,人心的温暖,是高悬的太阳。
武陵山山高路险。 十多年前,我和冉仲景去和当时在印江工作的莫伟、费飞马等人聊天。 当时武陵山区还没有高速公路,还是古老的碎石路。 下雨了,路湿滑,有悬崖有深渊,踩油门踩刹车脚都在发抖。 我不记得当时吃的牛肉是什么味道了,但梵净山脚下的臭豆腐和印江街头的玉莲茎,现在想起来还是让人垂涎欲滴。 如今,大部分公路和县城高速都在两小时车程内,最近的也只需半小时。 但交通方便之后,互动就少了。 也许岁月已逝,青春和诗都老了。
近年来,每逢春天,一群人经常以采茶为名去安达家吃农家饭。 安达佳位于贡茶和宜居茶的核心产区。 摘茶是假的,吃是真的。 当然,爱茶之人也可以赚一杯绿茶,尝试新火泡新茶。 一菊毛尖每斤能卖到几万。 文人没用,能泡出什么茶来? 真正能派上用场的,是在茶叶包装上写几个字,加上几行诗。 诗歌和诗人看似毫无价值,但也正是这样,诗歌才变得更加纯粹。 没有诗歌所附加的世俗气息,诗歌才能真正进入人们的内心,成为一种修养。 就算不能在世上使用,也可以白用。
3、诗人说:“我高兴得心虚。”
我在定市上小学时,李亚伟在定市酉阳三中任教。 无知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诗,什么是诗人。 多年后,关于李亚威的各种传闻流传开来。 原来他在定市工作的时候我也在场,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呢? 我想我当时一定是睡得太沉了,在一个又一个的梦中错过了那么多时空的交集。 浩瀚的青春,诗意的情怀,似乎只留给回忆。 据说,李亚伟在定城任教时,经常把课转移到周围的田野和荒山、荒坡上。 时有远方友人登门拜访,镇上摆碗招待客人不醉不已,十分方便。 那时交通不便,连县外的客人都感到很陌生,更不用说外省的客人了。
后来,李亚威离开了酉阳,关于李亚威的传说彻底变成了更加遥远的传说。 不仅对我来说,对很多人来说,李亚威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传奇。 比如当书商,赚了很多钱,开餐馆,或者中了奖,奖品就是某个地方有多少亩草地。 流浪路上的“鲁莽”,似乎预示着他的一生都在路上。 《豪猪诗篇》出版后,我立即买下来当枕边书读,但读得最多的还是《国文系》。
真正见到李亚威本人,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事情了。 他与一大批文友、诗人一起前往酉阳。 他们都在酉阳酒楼过夜,大声说话,喝诗。 李亚威就像照片中一样,粗犷粗犷,仿佛随时准备前往某个地方。 他根本不是诗人,根本不是徐志摩,一点也不温柔。
一年,李亚威的父亲去世,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诗人突然来到了这座小镇。 当然,其中最多的还是老诗人。 单从气质和长相来说,最有辨识度的就是李海舟、姚斌和杨戬。 大家在墓前摆了一张长桌,喝酒聊天。 不管熟悉还是陌生,他们瞬间就结成了兄弟,毫无违和感,魏晋风格很浓。 小城镇的气氛大多是传统和保守的。 这种情况即使不令人震惊,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。 真正的诗人不仅仅是行词的精神呈现,更重要的是深入到血肉里的内在品格。 它是一种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、生死观、伦理观、自然观、宇宙观。
创作长诗《大河去》和长篇小说《催眠师甄妮》的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冉冉,年轻时从酉阳顺乌江而下,在长江流域的涪陵读书、工作。江河与乌江交汇,后来又逆流而上,进入长江。 抵达重庆,将一生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文学领域。 冉冉在重庆作协工作多年,在文学组织和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。 对于冉仲景来说,他可以用五个词来概括:诗人、高级教师、非名编辑、好公民、胆结石患者。 看来,祖辈血液深处的诗意长河,依然在这位土司后人的身上流淌着。
小说家张万新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写小说了。 早年在酉阳县木材公司工作,后来在台球摊打工,又当过《小说选》的编辑。 小说里充满了很多关于木材的情节。 巅峰之作《马嘴鱼》中的叔叔是酉水河上支木筏的水手。 自从他与他的粉丝、博士生结婚后。 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医生张万新一直躲在爱情里,迟迟没有走出来,也没有迈出任何一步。 他“高兴得心虚”。 有一次,他和妻女到酉阳山老林的一户农家避暑。 我们一群人到达并杀鸡做饭。 饭煮好了,他从瞌睡中醒来,疑惑地问道:“你什么时候来?” 是的。 谁会最先从大梦中醒来? 生活就像小睡一样。 谁不会从午睡中醒来并再次从午睡中离开? 后来我才知道,张万新暑假的那座山,竟然是诗人魏巍的故乡。 这位从魏家山出来的医生,一有空闲,就会从西南大学新诗研究院跑回魏家山,或者叫上朋友,去村里做饭,享受山上的野风,或者独自坐在山上。一块岩石。 写一些关于白菜、月亮、鸡鸭、野猪、魏家山第一场雪的诗。
酉阳师范学校的老师二毛后来离开酉阳,从事了自己最喜欢的厨师工作——在京郊的一个仓库里开了一家餐馆,名叫天下盐。 李亚伟也开了一家餐厅,将餐厅命名为香记厨房。 天下岩后来成为北京文人墨客的聚集地,成为著名的文化地标。 二毛长期担任中央电视台热门节目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美食顾问。 诗人二毛出版了诗集《二毛美食诗选》。 写诗离不开吃饭,“我用春风炒青菜/雨滴给你炒”。 《道》、《碗里的国家》和《妈妈的柴火炉》。 在外人眼中,诗人的身份往往被视为第一身份,但在诗人自己眼中,诗人的身份往往是最后的身份。
由于种种原因,我无法再写下去了。 不要担心那些没有写下来的人。 如果我再写一遍的话,这个清单会很长。 另外,本文只是一篇随性文章,意在好玩、有趣,卖轶事,远非文学总结,更谈不上理论研究。 有人开玩笑说,诗人生活在历史里是神话,而住在隔壁就是笑话。 事实上,只有对此感兴趣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意义。 懂的人都懂,无需多言。
有时我会想,如果每个地方都住着几个作家和诗人该多好。 你的童年在这里,你的亲情在这里,你的爱情在这里,你的品味也在这里。 几位作家和诗人像你的邻居一样住在这里,和你吃同样的饭菜,呼吸同样的呼吸。 空气,诗意的栖息地。 就这样日复一日,有时突然打电话,电话接通了,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,只想打个电话。 然而,放下电话的那一刻,我的心仿佛春暖花开,天空晴朗。

有人说,家无书,田无草。 同样,一座没有作家和诗人的城市就是一座没有树的城市。 因此,有的城市优待引进作家、诗人落户,就是把大树种进城市。 从此,它们生根发芽,沐浴阳光、雨露。 这些作家、诗人给这些城市增添了诗意,为心灵提供了绿荫,带来了清爽的慰藉。
作者简介:狄米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 荣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马奖。
《星星诗论》2024年第3期
《星星》诗歌杂志
主编:龚学敏
《星星》诗歌杂志公众号
执行主编:肖蓉
协调员:任浩
编辑:黄惠子
提交邮件
《星星·原创诗》:
《星辰诗论》:
《星星散文诗》:
《星星·诗》: